
导 读
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奖励瑞典科学家、进化遗传学权威斯万特·帕博(Svante Pääbo),表彰他对已灭绝古人类基因组和人类演化的发现。

这是一位深深纠结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著名科学家。
他坦陈自己是诺奖得主的私生子,公开宣布自己是双性恋者,他致力于探索现代人类与古代人类的关系、古代不同人群的关系,他解开人类演化史中的一个又一个谜团。
30多年来,帕博以分子生物学分析基因序列,推演人类起源、进化、迁移,1997年以来对尼安德特人的研究更是做出了举世无双的贡献,推动人类对自己的了解。2016年,
《知识分子》有幸专访帕博教授,以飨读者。
撰文 | 陈晓雪
● ● ●

进化遗传学家斯万特·帕博(Svante Pääbo)| 摄影/艾维
正如一个小孩会问父母自己是怎么来的,作为这个星球拥有高度文明与智慧的动物,人类一直都在追问,作为一个群体,人类是如何诞生并发展到今天的。
从古到今,关于人类的起源与演化,人们提出过种种猜想,也试图给令人信服的解释。
在科学家试图还原人类演化历史的过程中,进化遗传学家斯万特·帕博(Svante Pääbo)不仅绘制出人类的近亲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图谱,还为古人类的研究贡献了宝贵的方法和技术,比如古DNA超净实验室。利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研究古人类和其他古生物,这使得古人类学研究增加了一个全新而重要的视角,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古遗传学(paleogenetics)。
斯万特·帕博1955年出生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他的母亲是从爱沙尼亚流亡到瑞典的化学家凯琳·帕博(Karin Pääbo),父亲为198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瑞典生物化学家苏恩·伯格斯特龙(Sune Bergström)。因为是非婚生子女,帕博从小跟随母亲长大。
在很小的时候,帕博就表现出对考古研究的兴趣,他的房间堆满了史前瑞典人制作的陶器碎片。十三年岁那年,帕博和母亲一起到埃及度假,第一次接触到木乃伊,萌生了研究木乃伊的想法。
因此,1975年最初进入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读书时,帕博在人文学院学习科学史、埃及考古学、俄语等课程。不久,帕博就失去了兴趣,两年之后,他转向医学,之后又读了一个分子遗传学的博士学位。读博期间,帕博接触到了DNA克隆的技术,产生了利用这一技术研究古人类,尤其是研究木乃伊DNA的念头。
1984年,帕博成功地从一个死去两千多年的木乃伊身上提取到了DNA,并分析了其中的一小段,其结果发表在东德科学院主办的学术期刊《古代》(Das Altertum)上。然而,当时的主流科学界鲜有人阅读这个杂志,无人注意到这一研究。虽有些沮丧,帕博继续践行自己的想法,尝试在细菌中克隆从木乃伊身上提出来的DNA。
1984年11月,当帕博想办法测序克隆出来的木乃伊DNA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个实验室报告了他们从一匹斑驴(quagga)的皮肤上提取出DNA并进行克隆,其结果发表在《自然》(Nature)上。斑驴是一种生活在非洲南部的动物,已经在1883年灭绝。也就是说,在帕博尝试利用DNA克隆技术研究古代人类时,也有一群科学家做类似的事情。与年轻的博士研究生帕博不同,该研究的负责人阿兰·威尔森(Allan Wilson)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演化生物学家之一,也是 “走出非洲” 的现代人起源理论的主要建构者。1987年,威尔森和其学生通过对全球现代人样品线粒体DNA的研究,提出现代人 “所有的线粒体DNA都追溯到同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可能生活在二十万年前的非洲,“线粒体夏娃”的假说对现代人起源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受威尔森等人工作的鼓舞,帕博决定向《自然》投稿。1985年4月18日,帕博的论文 “对古代埃及木乃伊DNA的分子克隆”(Molecular cloning of Ancient Egyptian mummy DNA)登上《自然》封面,引发学界轰动,很多主流科学媒体都给予了报道。
1986年,帕博拿到了自己的博士学位,随后来到瑞士苏黎世大学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后在英国皇家癌症研究基金(Imperial Cancer Research Fund,现为伦敦癌症研究所)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
1987年,帕博开始跟随威尔森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做研究。当时,扩增特定DNA片段的聚合酶连锁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技术刚刚兴起。在PCR技术的帮助下,帕博从威尔森实验室剩余的斑驴样品中提取出DNA并进行分析,测序的结果显示与1985年发表的结果相似。这意味着,古DNA的测序不仅可以更高效地进行,而且实验的结果能够被重复验证。
在研究从佛罗里达州发掘出来的一个7000年前的美洲土著的大脑时,帕博提取了一些DNA,并修复了一段看似不同寻常的线粒体DNA序列的片段,却发现它们此前在美洲土著人身上没有出现过,而只在亚洲人身上存在。经过两次独立的实验,结果依然如此。帕博很快意识到,这可能是现今的人的DNA污染造成的。结果确实如此。现代DNA污染是古人类以及其他古生物研究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尤其是在古人类研究中,即便是现代人皮肤上的一丁点颗粒都有可能毁掉最后的结果。
1990年1月,帕博来到德国慕尼黑大学,成为动物学研究所的正教授,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研究生涯。1997年他受邀担任马普协会在莱比锡演化人类学研究所的所长。
在德国,帕博的实验室专注于开发研究古DNA的技术。为解决DNA污染的问题,帕博和同事还搭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古DNA研究的超净室(clean room),并设计出超净室的工作规则。如今,超净室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古DNA研究实验室的标准配置。
尼安德特人是1856年在德国尼安德河谷(Neander Valley)发现的一种古人类。1997年,帕博和同事报告了对尼安德特人线粒体DNA的测序结果,这是科学家第一次从已经灭绝的人类身上提取到DNA并成功进行了测序。此后,帕博一直致力于对尼安德特人的研究。2010年,他与同事重构出在克罗地亚一处洞穴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化石的基因组草图,并发现尼安德特人与分布在欧亚的人群的祖先可能有通婚。2014年,帕博带领同事完成了对丹尼索瓦洞的尼安德特人的全基因组的测序,其精度可以与现今人类基因组序列相媲美。同年,帕博讲述自己和同事如何完成第一个尼安德特人基因组测序的著作《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 Man)出版。可以说,帕博是这个世界上最懂尼安德特人的现代人。
2016年9月初,斯万特·帕博博士来到北京参加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举行的 “人类演化与适应生存方式” 学术交叉研讨会。9月5日,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分子古生物学实验室主任付巧妹的陪同下,我们就帕博现在的研究、与中国的合作以及他的个人自传《尼安德特人》等话题聊了聊。
以下为对话部分内容:
已完成对克罗地亚尼人高质量基因组的测序
►知识分子:能介绍一下你实验室正在做的工作吗?
帕博:我们正在做的与之前的项目属于一个系列的工作。我们早先对位于西伯利亚丹尼索瓦洞(Denisova Cave)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进行了高质量的测序,它的质量甚至可以和现代人基因组的数据媲美。现在,我们测序了温迪加洞穴(Vindija Cave)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也做到了同样高的质量。温迪加洞穴位于欧洲南部的克罗地亚,所以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得到欧洲本地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因此,我们可以开始回答以下问题:这两个尼安德特人,谁与对生活在今天的现代人群基因有贡献的尼安德特人更为接近?很明显,克罗地亚的尼安德特人更为接近。
我们正在分析这个基因组(注:克罗地亚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的信息,并在上上周把数据上传到了网上(注:网址为https://bioinf.eva.mpg.de/jbrowse),这样全世界的任何人都可以很方便地得到它。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把整个基因组下载下来,和已知的现代人群的基因组进行比较。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个项目。
第二个,我们也打算研究更多样的晚期尼安德特人,尤其对45,000至40,000年前的晚期尼安德特人感兴趣——他们可能会在这段时间遇见早期现代人。我们想知道是否能够找到直接的证据,发现其祖先与现代人发生基因混合的尼安德特人。我们已经发现一些早期的现代人是尼安德特人的近亲,也知道尼安德特人对现代人有基因贡献,但如果换个方向思考呢?针对晚期的尼安德特人,早期的现代人对他们是不是有影响?混血的小孩是不是也会在尼安德特人的社会里生存繁衍?

帕博与合作者的研究发现,尼安德特人与非洲以外的现代人类大约在4.7万-6.5万年前发生过混血(绿色箭头),而尼安德特人身上含有现代人类DNA可能是两个人群在大约10万年前相遇的结果(红色箭头)。来源:马普协会莱比锡演化人类学研究所官网
最懂尼安德特人的现代人

尼安德特人基因组项目的部分成员,摄于2010年。来源:马普协会莱比锡演化人类学研究所官网
►知识分子:在遗传学领域,除了你的实验室,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实验室研究尼安德特人吗?
帕博:有,但并不多。我的意思是,其他实验室发表的论文不多。哥本哈根小组发表过一篇关于线粒体基因组的文章,我之前的研究生Johannes Krause(注:Krause曾是帕博的博士研究生,是解析已灭绝的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基因组研究团队的最重要成员之一,现为德国马普协会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所长、图宾根大学考古与古基因组学研究所荣誉教授)可能发表了一篇。所以,在尼安德特人领域,我们几乎已经做了所有的东西。
►知识分子:为什么研究尼安德特人的实验室不多?
帕博: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最早开发技术专门研究尼安德特人,而且我们专注于做尼安德特人。另一个是,尼安德特人供研究的骸骨也不是太多。我们是真正地致力于开发最困难的技术。研究古人类的遗骸在技术上非常难,因为你很难区分出哪些是污染,哪些是你真正要得到的DNA。我的意思是,研究古代的哺乳动物时,如果你找到了一段类似大象的基因,你就基本确定找对了。但如果你研究的是古人类的遗骸,比如说尼安德特人,当你发现一些类似人类基因的DNA序列时,你很难知道这到底是现代人类的DNA序列,还是古人类的DNA序列。我们的使命就是不断地改进技术,将我们能够测到的化石年份向后推进。我们今年1月发表了世界上最古老人类的核DNA序列,这是在西班牙发现、距今430,000年的早期尼安德特人。
现代人生存到今天不是偶然

重构的尼安德特人骨架(左)与现代人骨架(右)。图片来源: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知识分子:在研究尼安德特人的过程中,从开始到现在,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帕博:最让我惊讶的是,尼安德特人和我们的祖先发生了融合,对我们的祖先有基因贡献。更令我兴奋的是这一事实,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身上存有我们近亲的基因。如果将地球上所有的人类视作一个整体,从演化上来说,我们最近的亲人就是已经灭绝的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因此,我们可以研究今天每一个人的基因组,看看我们共有而尼安德特人没有的基因是什么。我认为这是对未来更重要的东西。
现代人和已经灭绝的尼安德特人以及其他灭绝的人群不同,他们开始发明技术,比如弓,人口的规模也开始变大。尼安德特人在某个时期可能有成千上万人,其他已经灭绝的人群也是如此,而现代人从过去的几百万最后发展到今天的几十亿。这是他们的命运截然不同的一个地方。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有助于我们找到现代人与他们结局不同的原因,我认为这也是关于尼安德特人最重要的东西。
►知识分子:尼安德特人灭绝了,而现代人存活并继续繁衍到今天,是因为我们更幸运吗?
帕博:如果 “幸运” 这个词指的是偶然的话,我认为现代人生存下来不是偶然。因为不仅仅是尼安德特人灭绝了,丹尼索瓦人也灭绝了,弗洛勒斯人也灭绝了。在距今4万年以后,就没有其他形式的人类存在了。这和现代人类的行为是有关系的,而不是偶然发生的。
►知识分子:现在还不知道原因?
帕博:不知道,但我认为可能与现代人发展文化和技术的能力有关。
►知识分子:尼安德特人存在的年代是什么时候?
帕博:啊,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们对尼安德特人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身材高还是矮,骨骼的特征等,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最古老的尼安德特人是40万年前出现的,最晚的可能是24万年前,但具体取决于怎么定义。尼安德特人的出现是一个积累、连续的过程,不是说一瞬间,Bang,所有的特质都出现了。
人类进化过程中特有的基因突变
►知识分子:除了尼安德特人,你还研究什么?
帕博:哇,还有很多呢。这十年来我们的精力主要放在了人类进化上。我们之前也研究过灭绝的动物,比如猛犸象、土懒(ground sloth)、袋狼(marsupial wolves)等,但我们后面就集中研究人类进化了。一方面是重新得到古人类的基因组,另一方面是研究现代人特有的突变,通过将这些突变引入人的诱导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也就是将细胞变回我们的祖先的状态,然后观察表型,或者在实验室的小鼠身上观察,这些突变发生以后会产生什么影响。
►知识分子:你们如何做到在老鼠的身上表达现代人类的基因突变,并得到这些基因的功能?
帕博:一些基因和蛋白在人类和小鼠之间(演化上)很保守,如果人类身上的某个蛋白发生变异,同时这个蛋白在小鼠中很保守,我们就可以通过小鼠研究这个蛋白的功能,其中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将来,我希望可以实现在小鼠身上建立起古人类中的一整条通路,或者把整个系统的一些组成部分换成类似古人类的。比如说,如果有一系列酶共同发挥作用,可以把小鼠中的这些酶都换成人类的,这样这只小鼠在某些生物学方面的表型就会类似人的。我们已经研究了一个叫做FOXP2的基因,我们将人类身上FOXP2特有的两种突变放在小鼠身上,观察小鼠的变化,发现这个蛋白质看上去有可能与人类的语言能力相关。这是这个蛋白质的功能之一。
►知识分子:这个基因突变影响到了老鼠的语言功能?
帕博:是的。当我们把在老鼠体内引入这两个突变后,老鼠发出的声音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而且它学习的速度在提高。因此,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研究老鼠理解人类身上的变化,当然,这个过程很复杂,毕竟实验的对象是老鼠而不是人类。
►知识分子:尼安德特人身上也有FOXP2的这两个突变,这是否说明尼安德特人拥有像现代人类一样的语言能力或学习能力?
帕博:我们不知道。从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来看,我们知道尼安德特人拥有这两个突变,但是影响语言或发音的因素可能有很多,我们目前并不是都很清楚。因此,我们并不知道这两个基因突变到底会对尼安德特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古DNA研究 “让我可以回到过去”
►知识分子:研究古DNA最令你激动的是什么?
帕博:某种程度来说,是我们能够回到过去,通过自己的技术解密古人类的遗传信息。在此之前,我们能做的只是研究现代人的DNA序列,使用不同的模型,猜测其背后的意义。现在,我可以真的回到过去,检测过去的信息,而且经常会有惊喜的发现。过去可能会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例如,巧妹研究了冰川时期欧洲人群的迁徙过程,而此前你并不知道这一过程,它只是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一个猜测,而现在你可以找到答案了。
►知识分子:你们实验室检测过的最早的人类的DNA是什么?
帕博:我们检测过的最早的古人类DNA是生活在43万年前,在西班牙胡瑟裂谷(Sima De Los Huesos)发现的。
►知识分子:43万年是你们实验室能够检测到的最早的古人类DNA,其他实验室呢?
帕博:最古老的DNA,我觉得可信的是生活在70万年前的一匹马的DNA,它是在加拿大的冰冻土层发现的,并一直持续处于冷冻的状态。哥本哈根一个实验室做的这个工作。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的论文声称能够做到几百万年前的DNA,但是我认为它们都是错误的。
►知识分子:为什么?古DNA研究有时间限制吗?
帕博:如果要我说一个极限的话,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大概在百万年左右。但是可以肯定的是,DNA在一定的时间节点之后就没办法继续保存了。但是我们可以做到40万年前的DNA,已经让我很惊讶了。我可能还会再惊讶一次(看到更早的DNA),但是我认为自然界的永久冻土也不能把DNA保存百万年。
现代人的起源问题要靠数据说话
►知识分子: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今天的现代人身上有1%-2%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贡献。科学家们已经知道现代人的起源了吗?
帕博:哇,如果一直往前回溯的话,人类和类人猿、猴子等哺乳动物有着共同的祖先。而现代人作为一个群体,在骨骼上和今天的人类区别不大。10万年到20万年之间,他们最早出现在非洲,然后扩散到世界,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和其他的群体或人群混合,比如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
►知识分子:“出非洲”和“多地起源”是关于现代人起源两个不同的假说,在媒体的报道中似乎呈现出一个相互掐架的状态。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
帕博:这样的掐架是媒体制造出来的 “假象”。实际上,这就像是碳14的测年方法,它可以让你从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发现中获取更多信息,知道其他的测年方法,比如铀-钍测年无法得到的信息。
我们要看到数据呈现出现的信息,不能一开始就觉得“有这两种假说,要么这个要么那个,肯定有一个是对的”。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拿现代人类起源这个问题来说,古DNA的方法揭示了更多根本没人想到过的问题。它清楚地显示出现代人不仅仅来自于非洲,因为我们体内也有来自尼安德特人的基因。但是在我们发现之前,我想没有人认为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或澳大利亚人身上能找到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因为根据连续性假说,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只应该在欧洲发现。所以这一发现真的根本没有基于任何之前的想法。
►知识分子:数据也有可能推翻以前的一些假说?
帕博:某种意义上说,分子遗传学家的长处是可以根据数据判断。好的研究不需要也从不从试图证明一个假说入手。你看到数据显示的东西,然后试着提出一些模型,解释你看到的变化。
古DNA研究需要更多考古学家的参与
►知识分子:古DNA技术在不断改进,古遗传学(paleogenetics)这个领域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成果。研究古人类,对考古学家的需求是不是没有以前多了?
帕博:不,情况恰恰相反。我们需要考古学家找到材料进行我们的研究,不是吗?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考古学家。或者可以这么说,我们只是需要一些特定的考古学技术,比如在取样本做DNA研究时,要如何避免处理样本时引入现代DNA的污染。但是,我们对考古学的需要是增加的,而不是减少。
►知识分子:有人认为,对于研究古人类来说,古遗传学的技术可能更先进,因此比考古学的方法更有优势。您如何评价这种意见?
帕博:这就好比说,碳测年技术出来的时候,给考古学带来了许多变化,但这并没有让考古学变得不那么有趣。实际上,考古变得更加有趣了,因为你可以从考古学家发现的东西上得到更多的信息。现在,古DNA技术来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一技术从考古学家发现的材料中得到更多的信息,而这让考古变得更有意思。我们是在考古学家发现的基础上做出发现的,如果没有考古学家的发现,我们什么研究都做不了。
更多的实验室,更多的合作
►知识分子:现在世界有很多做古DNA研究的小组,比如丹麦的Eske Willerslev小组,美国的David Reich组,澳大利亚的Alan Cooper小组。古DNA研究这个领域的竞争是否很激烈?
帕博: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一切看成是竞争上呢?我们一直一起工作、合作,比如我们和David Reich小组合作,一起发表了很多文章。我们依靠彼此。你不必把这些都看成是竞争。越来越多的小组一起研究古DNA,这是一件好事。
在我看来,这个领域从开始到现在,出现许多优秀的团队是件好事。二十年前,有许多发表的东西最后被证明是错误的。这让人感觉非常糟糕。我在我的书中曾经提到过这一点,我曾有过一种感觉,我们可以信赖的可能只有自己的结果,其他人发表的结果可能都是错误的。今天依然有错误的工作发表出来,但是你提到的那些研究小组都很优秀,发表的都是非常不错的结果。
►知识分子:你认为错误的东西比竞争还要让人沮丧?
帕博:我当然认为已发表的、很有说服力的东西被证明是错误的话,那是非常糟糕的。一些优秀的小组发表好的东西,也是非常美好的。我当然也知道,如果有人和你恰好在同样的研究(课题),而且他先发表了,你也会感到恼火。但是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因为这个领域有太多太多东西可以做。
►知识分子:你和哈佛医学院David Reich的实验室合作非常多,媒体也经常报道你们两个团队。你如何评价你和Reich实验室的合作?
帕博:我们两个实验室各有所长。他们(Reich实验室)在群体遗传学和分析数据上很有优势。我们一起合作,一起分析了第一个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他们在数据分析上给予我们帮助,我们在古DNA的技术上帮助他们。当然,两个实验室都是独立运转的。
遗传学的强项不是解释文明
►知识分子:关于东亚现代人的起源,有一些猜想:有人说是在东亚的现代人来自非洲,然后迁徙到东亚,有人认为东亚的现代人是由东亚的直立人连续进化而来。如果遗传学的证据显示东亚现代人的祖先来自非洲,这是否会有损中国的文明?
帕博:我想了解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不需要遗传学。这里有文字的记载,有文化的证据。文化的历史不是遗传学的强项。
我虽然不是很了解中国的历史,但是这个问题放在欧洲历史也是一样。比如,我来自北欧,当我来到希腊,站在那些古老的神庙前,不由赞叹,哦,那是民主的起源,那是建筑的起源。我感到这就像是我生命的起源,但是我自己的遗传信息并不来自于希腊,我的祖先也不是来自希腊。但是这并不重要,文化的历史才更重要。大部分的文化与文明起源于古希腊,但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真正的文化不是由DNA决定的,不是由分子决定的,对不?
►知识分子:是不是可以说,对于民族而言,文化是更重要的因素,而不是遗传信息。
帕博:当然,民族是属于文化范畴的。我的母亲(注:帕博的母亲为爱沙尼亚人)二战期间来到瑞典,我出生在瑞典,我也认为自己是个瑞典人,但是往前数一代人,我的DNA并不在瑞典。所以,文化更为重要。
历史上人类各个方向的迁徙都会产生基因流动。比如,去年德国接纳了超过一百万来自中东的移民,但这不会改变所谓的德国文化或文明。
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关注这样的问题。目前的研究过于强调基因。历史久远的尼安德特人,或者现代人起源的问题研究,我们缺少文字的记载,文化方面的研究证据,比如石器,也不多——石器是能够体现不同种族特征的研究内容。而对于近几千年来的人类迁徙历史研究,遗传学证据能够阐明的只占很小一部分,而且也不是最有趣的部分。如果你研究埃及,可以找到有文字记载的材料,通过阅读古埃及象形文字了解关于法老的历史,这可能会有趣的多。
与中国实验室的合作计划
►知识分子:刚才我们谈了您自己的研究,那么您与中国的合作怎么样呢?比如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IVPP)或者与付巧妹的合作?
帕博:我很高兴巧妹回到了中国,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实验室,拥有做这些工作所需的所有技术,并且做的相当不错。我认为在中国有个同一领域的实验室,能跟我的实验室做得同样好,会颇有成果。

►付巧妹研究员在做报告。 摄影/陈晓雪
►知识分子:能告诉我一些您的合作计划吗?
帕博:我的理解是,我们实验室的强项是开发和改进技术。当我们开发出新技术或者做出新改进时,我们很乐意把技术转到这里,这样巧妹就可以用它们研究中国的问题。我们当然也对这些问题和结果很感兴趣。我们想看看,比如,尼安德特人分布在欧洲和阿尔泰山脉的年代,你们中国的人群分布在哪里。我对这个很感兴趣,也希望巧妹能用我们的技术回答这个问题。
►知识分子:你认为中国在古DNA研究领域最有前景的是哪个方面?
帕博:嗯……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中国地域辽阔,有很多有趣的问题。但人类的历史也是与灭绝的动物相关的,比如熊猫的历史等等,有很多有趣的问题。这有点像,古DNA技术是一项可以广泛应用的技术。也有点像考古学中的碳定年法,可以应用于很多不同问题。(比如说,古DNA技术还可以应用在)病原菌的演化中,看几千年前存在哪些细菌和病毒。
►知识分子:中国境内存在尼安德特人吗?
帕博: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在过去的十年,古DNA研究的工作将尼安德特人的分布地点延伸到了西伯利亚南部的阿尔泰山,距离中国很近。尼安德特人可能出现过在中国,而古DNA的研究将在未来回答这些问题,比如历史上有哪些人群消失了,比如在5万年前或10万年前;这些消失的人群与尼安德特人是什么关系;他们与尼安德特人在遗传学上是否亲近。
《尼安德特人》是为家人而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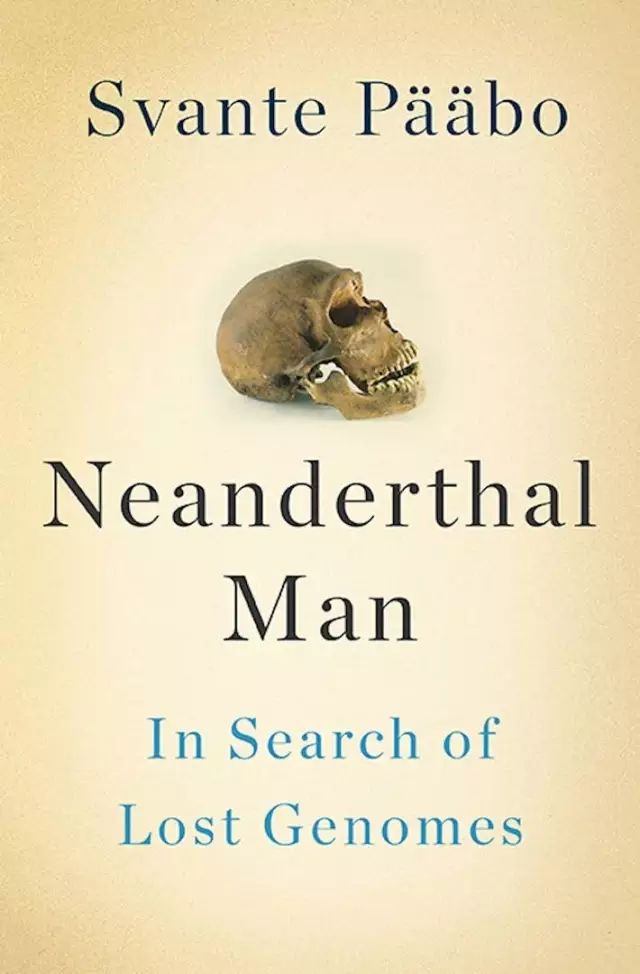
►帕博的个人自传《尼安德特人》
►知识分子:我们要进入最后一个问题了。您的著作《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 Man)明年就要在中国大陆发行了。你如何评价自己这本书?你有没有写其它书的计划?
帕博:没有,我不打算写别的书了。《尼安德特人》最后成了一个视角非常私人化的书,记述了整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一开始打算写一个严肃很多的科学书,但发现这样太无趣,工作量又很大。然后有一次我决定,不,我宁愿写一本我的两个小孩长大后能看懂的书,这样他们就知道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在做什么了。所以这本书更像是为他们写的,其他人想看也行。所以到最后,这本书的视角就显得很私人、私密。现在它已经被翻译成16种语言了,我挺惊讶的。
致 谢
感谢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为采访提供的帮助, 感谢彭若诗、陆绮和梅宝整理部分采访录音。
本文内容转载自订阅号「知识分子」,原链接:专访诺奖得主斯万特·帕博:透过基因揭示人类演化之谜


